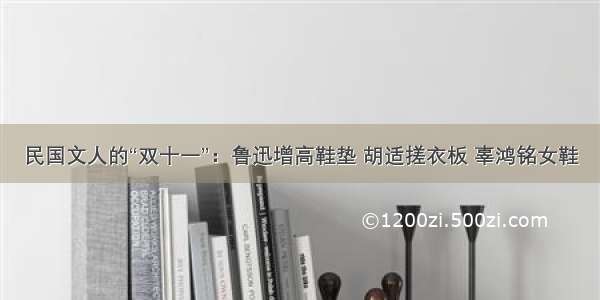老话说得好:“乱世出英雄,盛世产庸吏”,在军阀割据、社会动荡不安的民国时局之下,总能激发一些知识分子的创作灵感。
这些文笔犀利的知识分子,不仅用尖刀般的笔锋,书写批判现实的文章,还为民族大义牺牲自我、伸张正义。
这其中不仅有心系革命事业,批判人性虚伪的文学代表鲁迅,又有风流多情,文采出众的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。
不仅有天马行空、思想品味超前的思想大师胡适,还有通晓古今历史文化,又善于创作现代文学的作家郭沫若。
这些文人骚客,都是在中国近代文学圈比较活跃,和被人所熟知的代表性人物。
这就好比春秋战国时期“百家争鸣”的场面。
只是生逢乱世,文人墨客之间少了些“儒雅”的切磋,而是多了些不同层次的思想冲击。
而这些冲击,自然会导致一些口舌之争,通俗点说就是互相“骂战”。
这些骂战,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“厮杀”。
在这些文人墨客的互相“搏击”之下,民国文艺圈俨然成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。
这其中最为突出的,就是鲁迅与徐志摩之间,为一首中文翻译过来的波德莱尔的诗,引发的一场“争斗”。
1924年12月1日,鲁迅与钱玄同、孙伏园等人,一同创办了一个名为《语丝》的文学杂志。
当时诗人徐志摩有一部作品,是翻译自波德莱尔《恶之花》诗集里的《死尸》。
恰好这部作品要在《语丝》发表,而鲁迅又是该杂志社的主要撰稿人,对于徐志摩的这首译过来的诗,鲁迅则有其他看法:
其一,这首诗的译文,基本上与原著没有太大关系。
其二,徐志摩将原著里的词义,用中文夸大许多,甚至曲解了原意。
鲁迅向来追求现实主义的真理,对于徐志摩这种,追求诗歌富有音乐性的做法嗤之以鼻。
出于对真理的“维护”,和对扭曲“现实”而进行夸张著作的批判,鲁迅自然也没有对徐志摩手软。
徐志摩得知后,应该火冒三丈,血压直升。
对于新月派的代表性诗人,诗歌富有音乐性,不仅是追求,更是向往。
“我深刻相信世界的底质,一切和有形与无形相关的底质,他们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。”
从徐志摩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,他是一个追求精神上极度自由,甚至还偏向无形的神论色彩的人。
他们之间所谓的矛盾,归根到底,是现实派与抽象派的摩擦,但这也只是两人摩擦的第一步,精彩的还在后面。
1924年底,鲁迅又做了一首诗《我的失恋》,这首诗又是鲁迅反讽“某位”人物的诗。
这首诗原本是由孙伏园发表在《晨报副刊》上的,但是孙伏园却遭到副刊负责人的暴力相对。
无奈之下,孙伏园只好离职前往《京报副刊》,而《晨报副刊》就成了徐志摩的“天下”。
至此徐志摩开始操控《晨报副刊》,更是抵制鲁迅作品的产出和发表,将两人的敌对关系推向高潮。
想来两人都是读书人,都是中国文学作品的奠基者,如果不是对方的作品干扰到常人的理性思维,不会无缘无故遭人嘲讽。
鲁迅曾与叶公超聊天时,就直言不讳地批判:“徐志摩就是个流氓,他写的那些东西,都是无病乱呻吟”。
话到此处,顿时就明白鲁迅所写《我的失恋》为何意,旨在讽刺其不顾孕妻,与林徽因纠缠的情史。
“我的所爱在山腰,想去寻他山太高,低头无法泪沾袍,爱人赠我百蝶巾,回她什么:猫头鹰。”
“从此翻脸不理我,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,我的所爱在河滨,想去寻她河水深,歪头无法泪沾襟。”
这是鲁迅这首诗的节选,诗中没有华丽的辞藻,甚至都是朴实的白话,看似无力却暗藏刺针。
而徐志摩也毫不客气地回赠:
“鲁迅的作品,我甚少拜读,平日里发表些零星碎语,即使看了也等同白看。想看进去,需要很大耐心,看完一遍也会看不明白”。
这虽然是心如止水的轻描淡写,却蕴藏着十足的火药味。
鲁迅作为一个现实派的作家,文笔如尖刀,文风如铁枪,他善于用犀利的言辞,为人们扒开黑暗势力的外衣。
他体恤人间疾苦,歌颂敢于向恶势力斗争的勇士,也为身在水深火热中的穷苦人们,提供精神支持。
相比之下,对于徐志摩的散漫,以及超现实主义的诗歌,鲁迅更多的感受则是“华而不实”。
尤其是徐志摩,在妻子张幼仪怀孕之时宣布离婚,而又与林徽因交好,后来又缠上有妇之夫陆小曼,进而落得“渣男”的名号。
而徐志摩在其错综复杂的感情中产出的诗歌,更是让鲁迅这嗤之以鼻。
鲁迅在《三闲集》中,这样说过:
“之所以写《我的失恋》,是因为当时盛行“啊呀、哎呦、我要死了这一类情诗”。
“所以故意做一首打油诗,一来给‘失恋人’的安慰,二来纯属开玩笑用的”。
至于鲁迅所说的“哎呀、哎呦、我要死了”这种类型的诗歌,徐志摩在写给陆小曼的《爱眉小札》中略有“相似”之处。
“我的肝肠寸寸地断了,今晚再不好好地给你一封信,再不把我的心给你看,我就不配爱你,就不配受你的爱。”
“在如失望,我的生机也该灭绝了,最后一句话:只有死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”,此为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中的部分语句。
一个是铁手著文章的现实主义文学家,一个是风流多情的浪漫主义诗人。
一个对充满男女情长的“矫情”诗人的“无病呻吟”感到失望,一个对封建陋习盛行,情感得不到“自由”追随感到不满。
两人虽互相抵触,却又在各自的领域熠熠生辉着。
后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遇难,鲁迅也放下过往对其的一切成见,剪下报纸上刊登的徐志摩遇难文章,留作纪念。
虽说道不相同,可鲁迅心中始终为徐志摩留有一席之地。
两人都是中国文学史坛上的杰出人物,茫茫文海,互相暗自“较量”的文人志士数不胜数,这其中就有郭沫若与胡适。
他们两人,一个是坚定的革命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,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。
一个是战乱时期,游走世界各国疯狂刷新学历的,思想家、哲学家。
显而易见,这两人是两种不同精神世界里的文学家,都对自己执着的世界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坚持。
那么这样两种独特的生命体,究竟是如何摩擦出火花的?不免令人心生好奇之心。
首先,两人都是“五四”运动的代表性人物,但是胡适在文学造诣上,要领先于刚高中毕业的郭沫若。
当时胡适作为新文学的先驱,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,而郭沫若刚开始前往日本留学。
郭沫若之所以小有名气,是因为他曾在上海《时事新报学灯》上刊载了,新型风格的诗篇,并出版了个人诗集《女神》。
对于两人的恩怨始末,则是从一场不太愉快的“会面”开始,虽然两人后来各执一词,但总归是想互占上风。
那是19,高梦旦邀请胡适去商务主持编译所,接替自己的工作,胡适自知不能接下橄榄枝,遂婉拒。
后来高梦旦又邀请胡适做短期合作,这次胡适同意了。
197月,胡适抵达上海,高梦旦以及商务印书馆里的人都到现场迎接。
胡适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抛头露脸的“炒作”机会。
没过几日,上海商报就刊登一则《胡老板登台记》的文章。
文章里满是“新文学泰斗”、“月薪5000”、“总理以次”,“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,趋侍恐后”、“其阶级不是比政界更利害”等等诸如此类。
尽管胡适对外人说,这仅仅是夸大其词的“顽话”。
但这些刊登出来的话语,马屁拍的是相当有层次,甚至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
以至于胡适都不忍心错过这一期报纸,而将载有自己的部分剪下,张贴在日记本上。
对于此类的“吹捧”,胡适相当“适应”。
要知道当时郁郁不得志的郭沫若同志,曾经为了推荐自己的音译作品,就曾向商务主持音译所毛遂自荐过,然而却遭到了拒绝。
因为当时他还是学生,学生群体的作品少有杂志社愿意刊登,倒是更青睐于那些已经有名气的,比如胡适。
无奈之下,有一家上海的小书馆“泰东”,开出低价又恶劣的工作条件,接受了郭沫若与友人创办的刊物。
万事开头难,但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?
郭沫若虽然屈居于“泰东”,但是对于“商务主持音译所”的拒绝十分敏感。
巧的是,这次高梦旦在上海旦宴请胡适,郭沫若也收到了请柬,与其一同而来的,还有一起留学日本的同学。
后来胡适在日记里将此次会面记载为“高梦旦有意‘引荐’”,并且在日记里这般评价郭沫若:
“沫若君在日本九州学医,却颇有文学造诣,新诗十分独特具也富有创造力,但主题思想模糊,功力也不行”。
显然胡适对于郭沫若的评价并不是很满意,再加上高梦旦的引荐,胡适似乎并没有买这个账,这一次会面郭沫若显然被摆了一道。
对于那篇《胡老板登台记》,更不用多说,郭沫若肯定是嗤之以鼻,以至于后来与友人一起对胡适“口诛笔伐”。
新版诗集《女神》出版后,郭沫若也在文艺圈占有一席之地,对于早前在胡适这里受到的所有“压迫”,都如数回报。
198月,郭沫若在与友人一起创办的创造社里发表季刊,由郁达夫主笔,向文学“垄断者”逐一“开炮”。
胡适也难逃其“笔”,在《创造》第二期的文章里,有一篇是采用指桑骂槐、含沙射影的方法说道:
“我们中国新闻杂志界的人物,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,身体虽然肥胖得很,胸中却一点学问也没有。”
“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誉写几张,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,便算博学了。”
“有几个人,跟了外国的新人物,跑来跑去地跑几次,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,糊糊涂涂地翻译翻译,便算新思想家了。”
虽然当时有许多文学家都留学他国,翻译各大著作,但能称为“新思想家”的只有胡适。
此言明面上看,是针对大部分崇洋媚外的文学史者,实则剑指文学上的“资本”家胡适。
不管是不是指名道姓,反正胡适深感不适,他以一篇《骂人》,直言不讳地回击《创造》刊主创。
文中尽是“初出学堂的学生”、“浅薄无聊”、“无知愚昧”,等字眼来针对郭沫若《创造》刊发表的“粪蛆”一词。
1911月,《创造》又刊载了郭沫若《反响之响》,还有同僚成仿吾所发表的《学者的态度之胡适先生<骂人>的批评》。
胡适一个人单枪匹马地,与一个杂志社“战斗”,但胡适并没有惧怕,却越战越勇,骂战依旧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
19,胡适在《努力周报》上刊登了一则文章《编辑余谈》,继续以清高的文学泰斗的口吻讥讽郭沫若、郁达夫等人。
“我发表的《骂人》,竟有些不通英文的人,来和我讨论译文,我没有工夫搭理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。”胡适说道。
“假使你没有那么些闲工夫,便少说些护短的话!莫用你那高高在上的名气压人,莫用你北大教授的名号压人。”
“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、没多大斤两的东西、是压不倒人的,要想压倒人,只好请“真理”先生出来,请‘正义’先生出来”。
郭沫若一次性将这两年压在心里的所有不爽,一口气发泄出来,话到此不免替郭沫若同志痛快!
可见,不管处在任何一个时期,不论文人志士,还是达官显贵,只要和利益、权利沾染上关系,都会变得扭曲。
在利益权势之外,单纯地做一个简单的作家、诗人,是难以在乱世占有一席之地的,想要生存更是要善于处理各种“人际关系”。
骂战到这一阶段,《创造》社的成员,已经被文字带来的快感冲昏了头,而胡适这边却主动放下姿态,与其“握手言和”。
“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,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”,至此郭沫若、郁达夫便不再与胡适针锋相对。
这一点胡适就好过郭沫若,一个谦卑有礼,只是个贪图名利的白面书生,一个是直言不讳,敢于向垄断势力挑战的新型文学家。
不管他们如何用文笔“争斗”,最后都会为中国文学史坛留下无数佳作,文人逞一时口舌之快,世人享无数犀利佳作,利弊皆嬴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