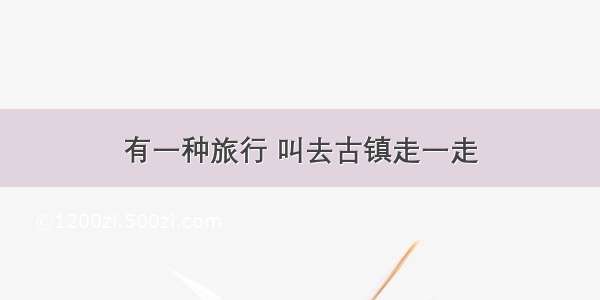有一种吆喝声总在我心里流淌,那声音温暖、热烈,伴着四季的风和雨,伴着楼头店(在玉壶方言里,店在这里不发第四声,而是念第三声)屋檐上的阳光,伴着下园南货特殊的气味,伴着店桥头穿梭的人流,伴着店桥岭青石板上清脆的脚步声,伴着店桥街此起彼伏的说笑声,伴着店桥尾浓郁扑鼻的酒香,从底村到中村,稠稠地弥漫而来,那么遥远,那么悠长,又那么切近,那么短促……“凉腐哎,凉腐哎。”“颜笠(玉壶话,斗笠的意思)哎,颜笠,快来买颜笠……”“虾皮,虾皮,新鲜的虾皮……”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店桥街是玉壶最热闹的地方,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。翻开《瑞安县志》,得以如下记载:据民国二十年调查,玉壶街长80丈,宽6尺,有店屋50座,商业76户。玉壶街即玉壶老街,位于玉壶镇中村。玉壶老街从上至下可分为:楼头店、下园、店桥头、店桥岭、店桥街、店桥尾。
楼头店和下园呈犄角之势:从楼头店向东经过十多级卵石台阶,就到了下方的壶山路、玉泉街和塘下街交叉路口,再沿壶山路前行,就是店桥头。从下园向东南方走约50米,也到了店桥头。两者合二为一。
根据玉壶人流传下来的说法是:至清乾隆、嘉庆年间,玉泉溪筏运业开辟,埠头在外楼岩坦碇。岩坦碇与天妃宫、店桥街一带距离近。渐渐地,店桥街、店桥岭、店桥头等地商业兴起。
店桥头分南北两侧,南侧原是大祠堂(也称新祠堂)围墙。上世纪60年代,底村将大祠堂边上的土地无偿转让给供销社、信用社、老邮电所和成衣社建房。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,供销社、信用社、老邮电所和成衣社相继投入使用。北侧是一间间店铺。
先来说南侧。关于玉壶供销社,我在《底村》一文中已进行采写,这里就一笔带过。对于信用社,我印象不深刻,因为那是物质相对比较匮乏的年代,谁家有钱存银行呀?平时我也很少来这里玩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,偶尔能见到有人来这里存钱。
信用社下首是邮电所。翻开《文成交通志》,得以如下记载:民国31年(1942),玉壶设置邮政代办所。翌年10月,玉壶邮政代办所由瑞安邮局划归大峃邮局管辖。1956年秋,在玉壶街尾设立自办邮电所,原代办所撤销。1958年4月,玉壶邮电所升为五等邮电支局。同年11月,因文成并入瑞安县,玉壶支局归瑞安县邮电局管辖。1970年,玉壶邮电支局搬至玉壶店桥头区委院内办理业务。1980年,在横山建造砖木结构三层楼房400平方米。翌年初,楼房竣工,支局迁至新址营业。
上世纪80年代初,父母都去了外地,每个月会寄给我20元生活费。我就拿着汇款单,到外村生产队队长家里盖一个“外村生产队”的印戳,然后拿到这里领钱。我每个月还会来这里寄信,一封平信的寄费是8分钱。汇取款柜台营业员是一名40多岁的男子,因为每个月都来这里几次,营业员熟悉我了,每次见到我,就会笑着说:“你爸爸又给你寄钱了?”有时,我想父母了,也会来发电报。有一次,我一连几天感觉耳朵一直嗡嗡响,就去发电报给父母,得知是0.4元/字。我想了又想,只写了5个字“亚病了,速回”,花了2元钱。三天后,母亲就赶回玉壶,带我去看医生。
邮电所下方的成衣社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。那时候,买布料要布票。一年到头只有到了换季,母亲才给我做一两件衣服,所以,我特别喜欢来这里看看。裁缝给人做衣服时,先用一把皮尺量了尺寸:衣长、肩宽、袖长、腰围、臀围等,用一块扁扁的粉笔记在布料上。然后,裁缝摊开布料,拿出一把竹尺,涂涂画画,布料上就有了直线和几何图形;接着,裁缝拿起一把黑色的大剪刀沿着划线“吱嘎吱嘎”地剪起布料,剪成大大小小的布片。最后,裁缝坐在缝纫机前缝起了衣服,随着缝纫机踏板“哒哒哒”声音的响起,一件衣服成形了。缝纫好的衣服一件件挂在成衣社西侧的墙壁上,红红绿绿的,煞是好看。每次一到这里,我就被这些衣服吸引了。
成衣社楼上是艺雕厂。据《文成县志》记载:玉壶艺雕厂于1980年创办,县二轻企业,主要产品有彩石镶嵌屏风及山水鸟兽、古代仕女等艺雕。除在国内销售外,还销往香港、荷兰、意大利、法国、美国、日本等国家和地区。后因主要负责人胡义锐出国,效益下降,1989年停产。这里雕刻的是一种名为“涂书”的石头(一位雕刻师告诉我,玉壶话的“涂书”就是青田石),是从青田进过来的,雕刻成花鸟虫鱼,山水画等。师傅会把雕刻下来的小“涂书”扔在地上,我们就经常来这里走走,看到地上有小“涂书”,跟师傅打声招呼,捡起来就跑。我们用小“涂书”在石头上写字、画画。“跳洋房”(也就是过间间游戏)前,拿它在地上一画,就会出现我们想要的图形。
成衣社的下首是法庭和大祠堂。胡希勃告诉我:大祠堂原本有一个戏台,有时有剧团在这里做戏。戏台下方存放着一个祠堂鼓,每到喜庆的日子,就有两三个村民抬着祠堂鼓来到店桥头,将祠堂鼓放在岩墩上。岩墩在上一截店桥岭y字形的口上,由鹅卵石砌成,高于路面约40公分,约有6平方米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,有人站在岩墩南侧,用力敲打祠堂鼓,那声音可谓是震天响,很多玉壶人都赶过来看,许多人还边看边唱,开心极了。后来,每当国家或政府有喜庆之事,祠堂鼓就敲起来了。也不知哪一年,大祠堂戏台被拆了,店桥头的岩墩也被拆了,祠堂鼓也不知去向了。
再来说西北侧。成衣社前门正对面的房子一楼在店桥岭,二楼在店桥头。二楼是一个房间,与路面持平。店主是一位畲族妇人,六十多岁,带有瑞安口音,声音略带沙哑,剪着齐耳短发,身体壮实,会给小孩“挑风”。
从我记事起,妇人就一直在这里。那时候,如果谁家有孩子不肯吃饭,就会被带到这里来“挑风”。妇人每次看到我们在街上跑来跑去,都笑眯眯的,很和善的样子,但一旦给孩子“挑风”,下手却非常狠。
有一次,我跟着外楼四面屋的一位阿婆来到这里,阿婆怀里抱着一个婴儿,说孩子不肯吃奶。妇人看了看孩子的舌头,叫阿婆紧紧抓住孩子的一只手。她拿出一根针,抓住孩子的另一只手,摊开,用针刺孩子的指节,再挤压指节。挤了好几下,婴儿的指节果然出现了一点无色的液体,妇人拿药棉擦一下。这根手指挑完了,又挑另一根手指,妇人一边继续挤,一边说,这孩子“风”吃起来了,很重。婴儿撕心裂肺一般地哭着,我吓得转身就跑,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,害怕也被抓过去。挑完“风”,妇人拿了一点草药给阿婆,嘱咐要熬汤给孩子喝。阿婆告诉我那无色的液体是“风”,孩子身体里有“风”,所以才不吃饭。由此,我有点怕这个畲族妇人。从那以后,我都不敢进那间房子。可有时我路过这里,还是能看到有孩子被带进去“挑风”。
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妇人不在这里了。大姑妈告诉我,妇人年纪大了,回上林老家了。我到现在也弄不懂,玉壶人所说的“风”到底是啥病。
供销社对面有一间药店,店主名叫清娒。清娒姓邓,姓名的最后一个字是“清”,玉壶人喜欢称男孩为“娒”,所以大家都叫他清娒医生。清娒医生约40多岁,中等个子,很和蔼。玉壶人都夸青娒医生医术好。有一次,一个孩子肚子痛被送到这里来。清娒医生摸摸孩子肚子疼的位置,说是有蛔虫,拿了两片蛔虫药给孩子吃了。不久,孩子的肚子就不疼了。
我小时候经常嘴巴溃烂,吃不下饭,到这里来买药。清娒医生给了我一瓶氯霉素药水,我涂抹一两遍,溃烂处就好了。我最喜欢这里的酵母片了,酵母片一分钱三粒,甜甜的,味道可好了,可只有在感冒过后不想吃饭时,母亲才会给我买几颗。
青娒医生不仅医术好,心地也很善良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我奶奶得了肺结核,家里没钱买药。在瑞安城里工作的舅公(奶奶的弟弟)得知消息后,赶到玉壶要带我奶奶去上海治病。生性倔强的奶奶坚决不同意。舅公没办法,只好一次次买了治疗肺结核的西药,外加一“砖头”(玉壶话,小砂锅的意思)的猪脚送到玉壶,给奶奶吃。有一次,我看到舅公临走时眼睛红红的,嘱咐我奶奶一定要记得吃药。过了一两天,奶奶叫我跟着她去卖药。我和她走到清娒医生店里。清娒医生说我奶奶已经来这里卖两次药了,这次无论如何也不买,叫我奶奶把药吃了,不然会连命都没了。奶奶说家里没钱“买配”(玉壶话,买菜的意思),清娒医生说可以借钱给奶奶,但好强的奶奶不同意。最后,那一大包药卖了9.1元钱。奶奶拿着钱走出药店门口,清娒医生还在叫,以后别来卖药了,自己吃吧。年幼的我看到奶奶和清娒医生两人眼里都含着泪水,我从泪水中看到了清娒医生对我奶奶的关怀,也看到了奶奶的无奈。这是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的悲剧,也是时代的悲剧。奶奶拿着钱,去店桥街买了肉和虾皮,分给我妈妈和婶婶。上世纪80年代初,奶奶就“走”了。
从我家(外楼四面屋)去店桥街要经过店桥头。店桥头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地上的“烟酒”灰。那个年代,抽香烟的人不多,农民一般都是种了一种名为烟草的植物,到了深秋,摘了烟草叶子,放到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阴干,再切成丝,这种烟丝就是晒烟,玉壶人则称之为“烟酒”。再去挖一根细小的竹子(要连根挖起,竹子的根部做烟筒头)做成一支烟筒,把“烟酒”放在烟筒头上,点燃了就可以抽了。玉壶人管抽“烟酒”为吃“烟酒”,吃完“烟酒”,就把“烟酒”灰磕到地上。
那时候,我和姐姐每人都只有一双布鞋。有时,我们把鞋子洗了,就要赤脚了。儿时的我喜欢跟着姐姐,她跑到哪,我就跟到哪。姐姐和小伙伴跑过外楼路,向店桥头跑去,我就一路追过去,跑着跑着,到了店桥岭y字形口上的店桥头,经常一脚就踩到滚烫的“烟酒”灰上,烫得直跺脚,然后哇哇大哭起来。姐姐早就跑得不知去向了。哭完了,我就一颠一颠地拐着脚走到镇政府(大祠堂)的墙边,那里有一条从镇政府食堂伸出来的水管,水管里的水清清凉凉的,偶尔也很暖和。我把脚伸到水管底下,冲冲水,然后慢悠悠地回家。
有一次,我的右脚被店桥头的“烟酒”灰烫了,起了一个大水泡,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,溃烂了,好长时间走路都有困难。
与岁月对望的店桥头,许多年前变了样:从外楼路至店桥头的鹅卵石路面都已经成了水泥路,成衣社、石雕厂、信用社、邮电所和供销社都已成了一片空地,其外侧砌起了围墙,供销社对面建起了高楼。
一切都与原来不同了。
深夜,随着歌曲《成都》那熟悉的旋律响起,赵雷的声音缓缓划过我的耳边:“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,一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,也不停留……”莫名地,我也想起了玉壶的店桥头,我也想到店桥头走一走,再看看那里的灯光,再踩踩那块土地,再听听那干脆利落的玉壶方言,再站在大祠堂的墙外,让玉壶镇政府食堂水管里流出来的水冲冲脚……
本文由胡晓亚提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