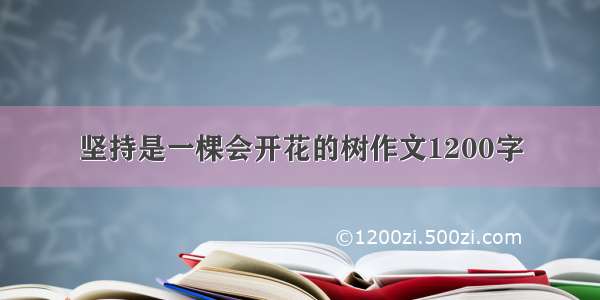《作品》
陈泽源
(级本科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)
李家结婚了,他说那天日子好。我觉得没错,因为今天这一条路上的树颜色很美。让树好看的从来不是色温,而是石色的路。
我很喜欢李家的哥哥,他大我五岁,人意识增长最快的五岁。他说学院的老师都喜欢屎,而非他的作品。我觉得没错。我的老师也从来不喜欢我的作品。
他最近的一部作品获了奖,一个等同于安慰奖的,不记得名称里放的是“人气”还是“精神”的奖。他不以为然,但他父母很开心,包括今天和他父亲结婚的这个。他说他后悔告诉他们,他还是习惯他们叫他去死。我觉得这句话是错的,和他父亲一样是错的。
作品里讲了几百年后一个人的小腿要被切下做成肉串,他便跑。最后跑上了三桥。在三桥的另一端是海边的山河树林,但他没能过去。在被包围的时候那人羡慕地望向远处,那里是被炸毁的一桥二桥。
他说看待事物不能用对错来看,我觉得很好笑,因为对错就是勾和叉,我们从小见到的就是勾和叉。他妈妈给我看他小学作文全是波浪线和勾。只看到过有一次,一条均匀的波浪线下面:
“这个父亲节你不要去找外遇,老实在家待着”
这句话被打了半对半错,是他给我看的。他的初高中作文全是叉。
在我想着之前那个作品的时候,她上了车。要证明一个作品有多烂只需要有什么让它显得可笑就可以了,而她就坐在我边上,脸颊中央有一丝丝红,像刺在上面,分不清是疹还是晕。她叫乐乐。
“靠座椅上吧”,我说。她不肯,什么都听不见似的。但她能看见自己母亲坐在前座,抱着半血缘的妹妹。旁边我的父亲踩了油门,她随着车的起步而摇摇晃晃。我继续想着自己的那个作品。
车子到了小巷,前面就是她外婆家大院。我下车把后备厢的垃圾带出。这只手的手肘被伤到了骨头,肌肉毫无作用。可我还是没有换手。不出所料,我的父亲等不及了。他发动车子,垃圾在后面拖了一地。这样也挺好,我们两个人都能怪罪到对方。我们都有人可以怪罪。
但我没有,我不想让她看见。只是听他摇下车窗,声音越来越远地骂着些什么。等我把垃圾收拾好,走进门口的时候他们已经上了餐桌,但无人坐下。
父亲怕她的肺炎未愈。妹妹被母亲抱着,她站在那儿,被椅子挡着的父亲问个底朝天。房间里全是油烟味,窗外是山,山上的地里都是些塑料袋子,山下的屋檐却干干净净。她外婆外公在厨房,我不知道吸这么多油烟他们是怎么活到现在的。我打开窗,用没受伤的那只手。
“你奶奶有没有带你去过医院”椅子说。
“她奶奶怎么会带她去医院。妈妈给你买的发卡呢,发卡是不是都被拿去给弟弟了?”她在证明自己和他们不一样:乐乐的奶奶,奶奶曾经家暴她的儿子,还有我父亲。但他们的语气一模一样。
田野里站着我,晚霞就在路中央。这云就跟电线杆子一样不动,但依然有风驱赶着我。
我沿路去李家,每一处被路横贯的田埂下都出现着垃圾。出了田野,围墙内有人打着羽毛球,看门狗朝我的背影叫。我终于走到了李家,哥哥在和他父亲吵架。
我知道李家的父亲是错的。哥哥在我面前唯一对他的认可就是给我看过他父亲年轻时拍的照片,拍的是她母亲。构图都很好,就是总局部过曝。他父亲说,现在谁还拍胶卷。他说他的相机在台湾爬满了真菌,他都不想去洗。而我已经拿压岁钱买了一部胶卷相机,正在担心长途运输会使镜头发霉。
哥哥知道把乐乐送回去意味着什么。他上一次这样歇斯底里还是颁奖后对他父母。
我知道此时他也羡慕着一桥二桥。他说一桥二桥象征着死亡美,仿佛世界上所有死亡的警告都由它们发出。使将死的知道自己将死。前提是对死亡有体面与美丽的追求。
但我没有,我还企盼着那台胶卷相机。如果我边上的人咳嗽或者三十八度,我会离他远点。
我还知道没有人能表述出那股羡慕。因为几百年后,语言和镜头一样不再用来表述感觉和美,所以尽管人们还是说个不停,语言还是退化迨尽。
她外公给我倒满了一杯黄酒,我很讨厌这里的土话,我从来没听到这些说土话的人说出过任何美的东西。另一边,她妈妈在给她扎着辫子,说她戴着的发卡就值几毛。
“叫乐乐的一般都不太快乐”。
虾子被端上来,窗外的山之前没有垃圾,所以这里的人们还会跑别的地方去买虾子。
“为什么”她妈妈说。
“因为这么取名字的人都缺心眼。我以为你们给妹妹取的名字已经够烂的了”
“妹妹的名字多好。”
“她跟她名字一样蠢,爱看《小猪佩奇》的都很蠢。”
乐乐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似的,她的眼睛在思考。辫子扎好后她去找妹妹玩,父亲把妹妹抱远,她倚到柱子上看着四周。在他经过我时我说你和以前一样混蛋,尽管我知道他会说什么。我每次都要听到人们说别人知道他们会说的东西。三桥对岸有猿,不知道他妈的多少年之后世上就只剩它们会说爱,大部分还是假的。所有人都上了餐桌,我父亲和他叫的父亲继续聊着口罩生意。之前我采购来那批时被坐地起价,他骂我好像自己不这么做一样。
“妈妈我在奶奶家总是很想你的,我今天很高兴你能来看看我”。我终于知道她话不多不是因为不想说,是她说得太不熟练,像妹妹一样。
我喝下了第一口黄酒。父亲说想去山上找找笋,她外公说山上什么都没有,都是垃圾。
“妈妈我每次哭都是你救我”乐乐说。
“她说什么”我说。
“她说她每次哭都是我救了她,我也没听懂”
她外公说这里的黄酒很好,我说好厉害,我喝不出区别。
她外公问我念什么专业,我说我念戏剧。
“搞艺术的”。
我不想说我在念艺术。一些人在艺术观念上的垃圾与自大让我只想叫他们去死。很可惜,这里有些就是我目前的老师。这让我甚至原谅了把我手打伤的人。
但我并不因此记恨我的父母。我不用在讲台下被浪费时间,也不用在他们感冒时在群里刷“注意身体”。除了那次领奖,我在台上说了那个人,我知道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。我不爱他,但我爱他的作品。我说我能为了践行他的艺术观去死。回来我的父母问为什么不说感谢他们的话语。我发了疯地想把这股吃屎感扔回去。但说完我就后悔了,像后悔去领奖一样。我居然和他们讲这些,我像那个小女孩一样在和妈妈说哭。
他们看我的眼神也印证了我该后悔。我曾为了看一眼星空跑到新疆,火车贴着天山,但窗外什么都没有。星星也看不见。等我乌鲁木齐见到接待我的那个客户的时候,我跟他说我要看一眼星空,他也以这种眼神看着我。
黄酒已经凉了,我把最后几口喝掉。客厅跑着乐乐他们,我去了客厅。她跑完咳着嗽。
“幼儿园有人欺负你吗”我仿佛没别的话语可说,一上来就想做别人的救世主。我好像和我小我五岁的朋友一样整天说着对错。但现实确实很多是被定义了对错的,颁奖典礼主持人用“好看”形容我爱的作品是错的,微博发什么也都是充满了对错,
她说幼儿园没人欺负,奶奶会。我问她家多大,我让她被打时就跑。她不愿意。
“你抱我”
我被她吓到了,茫然地盯着她,好像我小她五岁。
“你绝对抱不动我的,我很重”
我自责起自己。我想起我在台上说的那个人,给他书写序的把他的想象力比作了生殖器。永远都是这样,让自己同处一个艺术阶层就想办法把它和生殖挂钩。低劣也是不可攀的。而我刚刚就很低劣。
我把她抱到屋外,他们都出来了。
郊外星星也不多,但特别亮。我说这里星星好亮。
她说星星很丑,我知道我带她去看那片晚霞她一定也会说很丑。
我看了看她,我对她说你看不见星星了,一张火车票就能换来的星星。
但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多的是。
回去路上,我想教她写自己的名字,这部手机不等她划完一个笔画就识别出一个外星符号,可我没纸,她也不会握笔。
她说她要听《虫儿飞》。我问为什么,她说她要听。
我去搜这首歌,搜索引擎推荐着“父母离婚小学生作文,看哭了无数网友”。那张图里划满了波浪线。音乐网站的歌都放不出来,我快没了耐心。我点到早教音乐。放出来的编曲是多么低劣,低劣到不可攀。但她听得很沉醉。更低劣的东西还在时时被制造出来,我现在只希望她不要被它们侵蚀,尽管这是迟早的。
“她为什么喜欢这首歌”我说。
“之前胎教的时候经常放”
窗外是烦,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多的是,但不在窗外。我要回去做作品,在这之前,还要写些没有意义的破作业。
“妈妈,我回到童年了”她把身子挤到了前排,随着车的起步而摇摇晃晃。
“你现在就在童年啊”她母亲说。
“我回到童年了”
“你现在不是就在童年吗”父亲终于不用从后视镜看我们,他之前一直在这么做。
车到了,但第二遍还没放完。她母亲在催她,她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似的,直到把我手机拿走。我不知道她们到家门口时,这首歌有没有放完。
她母亲把手机递给我。
“这是什么”后视镜说。
“他手机给她放音乐,还给他”
“你把手机给她忘了还,我还要再跑一趟来取”
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老师,她让我写这个小女孩从武汉过来,“强化她的无家可归”。我再说了一遍她的父亲可能感染了肺炎,回来时传染给了女儿。她说这不能够强化,且不合情理。我知道武汉在这些“戏剧头脑”里就跟这个小女孩一样。
我知道她没有回去。她奶奶只会把她送出来而不会迎接她,所以只需要等母亲离开。她会走之前的那条路,到田野中央,什么都没有的地方。声音来自远处的高速公路,被一排树挡住了亮光。
她站在那。
我想下次她见到我时一定会对我说,没出来时想看到的一定是这样的。我觉得不对,她说她想看到的是这样的。而我,根本不知道自己想看到的是什么样的。
她没出来时小我十五岁,尽管才没多久她就已经这么成熟,成熟到知道这些话对她妈妈讲是没有意义的。
清明的路上,小男孩走在后面,扛着一人高的花朵。他嫌母亲走得太快。雾霾使所有颜色都失去了通透,但树还美丽。
关卡收走了所有的纸钱、元宝和香。
等母亲把墓擦完,他把衣服掀开,银船——他这么叫它们,还贴在圆肚皮上不肯下来。“在这里陪会爷爷”火机被一块收走了,母亲要回到车上去取火柴。
他不知道说什么。他抬头好似要花很大的力气。不是为了看爷爷,他喜欢远处那行树的颜色。
银船被点起来,烟把巡逻的人们吸引过来。
“快再点根火柴”
他才拜到第二下,鞠躬不闭上眼。他要读墓碑上的名字,读上面的妻、儿、孙。他每次写作品都缺名字,他不会取,只能让数字和数字相爱。远处,火车驶过无缝钢轨,中年女人刮着纸钱灰,殡仪乐队的瞌睡鼓点低劣地吹奏出流行歌曲。
供稿 | 陈泽源
编辑 | 冯晴蕾